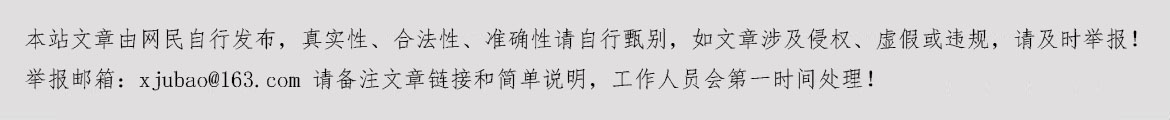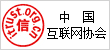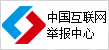一场漫长的上海逃跑计划,中断在浦东机场
2022-05-27 16:56:01
一群从上海“跑路”失败的人,被迫卷入了一场生存实验——没床、没固定食物、没公共交通工具,如何在机场、火车站流浪一个月?
这群“跑路”失败的流浪者,几乎囊括上海的所有“社会面”——底层打工人、都市白领,飞加拿大、瑞士、新加坡的“出海派”……
所有人都措手不及:在城市文明笼罩的大都市里,人们被迫缩回某种原始的生存状况,被最基本的出行、食物、居住需求团团困住。
我们找了几位上海浦东机场(特指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)的滞留旅客,大部分人都在机场生活了半个多月——有回不去高考城市的准高考生Mikey、从外地支援方舱的“方舱大叔”海哥,徒步二十多里地到机场的山西小哥张允,及飞加拿大、瑞士等的“出海派”等。所有人中,至今有一位仍滞留机场,其余人都成功离开了上海。
以下是他们的“跑路”故事与被困机场生存指南。
千军万马的艺考,过不了空无一人的登机口
浦东机场的流浪者,个个都有夸张的“机票取消”记录。
4月15日,上海官方疫情发布会明确表示允许外乡滞留人员返乡后,Mikey就开始疯狂抢票。他是吉林长春人,一年前来的上海“艺考”学校。前不久,他收到了“梦中情校”——北京电影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艺考通过通知,急着回家补高考文化课去。
Mikey惨不忍睹的机票取消记录。/图源:Mikey
他买过上海直飞长春的机票,还有飞大连的、飞上海周边城市的机票,全都被取消了。回家无门,于是他另辟蹊径地买了从上海飞青岛,青岛转机到大连,大连转机到烟台,最后从烟台飞长春的四张机票来“迂回救国”。结果,航空公司很“鸡贼”地先取消了最后一班,接着取消中间的航班,让他怎么都飞不成。他心如死灰,“现在四张票里还有没取消的呢,等着吧,过两天绝对就取消了。”
在机场待的时间越久,他买机票越是无底线妥协。有一次,有内部渠道告知他有飞“辽宁通辽”的机票,他内心窃喜,飞辽宁好啊!结果,他查了半天,才发现这是飞内蒙古通辽的机票,跟他家隔了十万八千里。但他还是买了,“只要能飞,去哪儿都成。”
过去的5天里,他的机票被退了一万八千块钱,每天平均要退三千六百元——也就是,一天差不多要退3张机票。
浦东机场,候机的人与被滞留的人。/摄影:Mikey
算了算,他的机票一共被取消了20多次。他心急败坏地说,“是说让你返乡啊,没说机票取消率100%啊。”航空管家2022年3月底的数据,也印证了这一点——大型机场取消率前三的是长春龙嘉(100%)、南昌昌北(97.0%)、沈阳桃仙(95.1%)。
但机票取消时间相当“狡诈”,Mikey说,他每次致电航空公司,对方都只会甩锅道“我们不知道,但取消的概率很大。”就像一个“渣男”,不跟你明确提分手,就一直吊着你。利用售出机票到机票退款的这段时间,“他们可以拿你的钱去赚利息,最大程度地榨干你。”Mikey看懂了套路,却不得不入套。
航空公司最“狡诈”的一次是,Mikey第二天一早的飞机,当天下午都没取消。他心想着,“这回该让我飞了吧”。
于是,4月25日当天,他被迫签了“解封前不返校”的承诺书,头也不回地走出“艺考”学校,想尽办法搭了辆警车到浦东机场。当一切准备就绪时,他手机突然跳出一条短信,“因公共卫生原因,您的机票已被取消……”
就这样,学校回不去、附近酒店又少又贵,还可能被临时征用或封锁,Mikey就这样被迫住进了机场。
近期飞泰国曼谷的姑娘木子,倒是提前预订了浦东机场附近的酒店。坐出租车去酒店的路上,酒店还回复说能正常入住。可二十分钟后,当她抵达酒店时,却发现门口站了一排“大白”——酒店被临时封了,只进不出。
因此,睡机场成了他们最保险的做法。
浦东机场的“滞留链”
“方舱大叔”海哥与山西小哥张允,跟Mikey前后脚住进浦东机场。他俩都准备飞国内北方城市。
当然,想在封控期间进浦东机场流浪,如果没有一张被取消的机票,外加48小时核酸证明,都不够格。有一次,Mikey前脚从浦东机场踏出,花几秒钟取了份外卖,后脚他就被安保拦住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。
一旦踏出机场出口半步,没有48小时核酸证明,休想再进来。/摄影:Mikey
“方舱大叔”是3月份跟几个同乡从老家山东烟台出发,坐了辆货车到的上海宝山区某方舱医院。大叔在方舱当保安,工作了一个月后,听说家中的老父亲身体不太好,他便急着回家。这份方舱的工作是他跟招聘中介谈的,几百块一天。临走时,由于没干满规定的时间,大叔还跟中介闹了点不愉快。
跟“方舱大叔”聊天时,他已在机场滞留了一个多星期。得知我的来意,他第一句话就是,“现在要帮助,就是(让我们)赶紧离开上海。”他操着一口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,急躁地说,“我们冒着生命危险,随时可能被感染,来支持上海、帮助上海。现在连家都回不去,真是气人。”
说罢,他还着急地冲我打听,“你是记者啊,我得到一个消息,上海有各省各地的政府派专车,给我们这种志愿者拉回去隔离,是有这个事情吗?”
Mikey在机场经常充当“方舱大叔”的“翻译”,“别人听不懂他说的话,我就给他们翻译一遍。”他说,“方舱大叔”年纪大了,不太会用手机,也不会抢票,打探消息基本靠口耳相传。
山西小哥张允住在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,这里有片“城中村”——由于房租低廉,成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大本营。上海疫情开始后,他们这帮“打工人”的生存境况估计比住小区的人更差——抢不着菜、揭不开锅。可山西小哥刚从“城中村”逃出,就又被困在了机场。
好在,Mikey、“方舱大叔”跟山西小哥张允都是北方人,几个人看彼此都贼亲切,索性就抱团。三人有饭一起吃,睡觉在一块,票也一起抢。滞留机场的这段时间,他们三人抢着被四五家媒体采访了一轮,成了机场里的明星。“可我现在,就像个乞丐一样……”,山西小哥无奈地说。
被困浦东机场的滞留旅客,大致分为飞国内航班与飞国际航班两派,各自抱团。国内航班的取消率极高,这一派也因此人多势众,内部还按南北方划分了小圈子。
相比之下,国际航班是最准时的,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被落在了机场。上海跟东京两地飞的龟田,在浦东机场遇到被滞留好几天的“苏黎世大姐”与“多伦多大姐”。这两位大姐,一个是飞瑞士苏黎世,另一个飞加拿大多伦多。
龟田说,“苏黎世大姐”是大连人,来上海转机时,没想到被滞留了。龟田飞走的当天早上,“苏黎世大姐”还处在机场新一轮机票取消的崩溃中,可当龟田抵达中转城市时,“苏黎世大姐”也已从浦东机场脱身,顺利到韩国转机去了苏黎世。
Mikey说,只有他们这群飞国内北方城市的,处在浦东机场“滞留链”底层。
每天,只要身旁有一架飞机起飞,都能瞬间刺激他的神经。“刚才听到没,又有一架飞机起飞了。”他在机场目睹了几十架飞机起飞,“飞加拿大温哥华的、加拿大多伦多的、新加坡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。前不久,还有飞广西南宁的。”
每天,寥寥无几的航班,几乎都是飞国际与港澳台的。/摄影:飞温哥华的姐妹July
Mikey身后的停机坪。/摄影:Mikey
Mikey说,他甚至在机场看到过一家人上午到的机场,下午就包机回了四川成都。这件事极大地刺痛了他,“你要说航班不能飞,这我认,但他们包机走是啥意思呢?”
Mikey没在机场看到一架飞国内北方城市的飞机,他们这群人,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,困在浦东机场的天花板下不得翻身。
撞见飞走的旅客登机时“拖猫带狗”,Mikey内心嫉妒得都快滴出血来,“猫猫、狗狗都能上飞机,我上不了。”
而对于那些连机场都到不了的人来说,Mikey已经是被羡慕的那个了。
去浦东机场的路——徒步、单车、警车
在上海交通几乎停摆的状况下,要想从家到浦东机场,只能各显神通。
外地人去浦东机场的路,是最通畅的——通常,他们只要先坐高铁到虹桥火车站,在火车站花几十块钱就能打到去机场的车。
而上海市民想从家打车到浦东机场,却要在“黑市”上花高于市场价近20倍的价钱。据几位租车公司老板的报价:上海市内,包车起步价800元;跨区的话,1500元左右。一位住酒店的旅客说,他打车(跨区)开了十几分钟,就花了1200元,这还是让酒店前台争取的协议价。
老板阿冯有一家租车公司,公司的车常年在宁波与上海等地跑。上海这波疫情开始后,他们的车被征用为防疫用车,拿到了上海市政府给的“临时通行证”,成了上海车中的“特权阶层”。
上海允许“返乡”后,阿冯的这些车顺利成了“返乡车”。他得意地向我展示:“从上海回大连的美女,已经成功到达——对方出发前给了一万块押金,抵达后给了一万二,共两万二千元。明码标价,童叟无欺!”
上海市政府发的临时通行证。对封控期的上海司机来说,可谓一证在手,天下我有
宁波租车公司老板的收账截图
可Mikey觉得这分明是在抢钱,他宁愿在机场继续死磕,都不愿坐“黑车”:“这个b白赚我几万,我还要坐在他旁边,感受他的呼吸、感受他英俊的面庞跟龌龊的头脑……”
为了不花冤枉钱,从学校去浦东机场的时候Mikey直接打110找了警察。据官方口径,上海民警接的单中,50%都是求助出行、就医类的问题。理论上,这条途径是可行的。
但得知Mikey要回去高考,警察先让他出示了准考证,接着问了他一句,“为什么准考证上没有写明日期?”警察还告知他,必须在14天内高考,才能开“绿色通道”。Mikey当场被这些“套话”气笑了,“我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,不是小升初考试。”
再加上,如今从上海回长春,难免不在其他城市中转,并就地隔离14天以上。回到长春后,还要接着隔离。所以“14天内高考,才能返乡”的规定,不免有些可笑。
最终,Mikey通过朋友联系上另一个警察局,顺利坐上警车到了浦东机场。
去机场、火车站沿路的检查站。/摄影:上海市民付先生
山西小哥张允更加生猛,他一个人连背带扛几十斤行李,从浦东新区曹路镇出发,徒步了二十多公里地到的浦东机场。他整整走了5个小时,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,只偶遇了一个男人牵着俩小孩走过,路边连辆共享单车的影子都看不到。
路是手机地图导航的,有几条小路是被铁丝网封住的,山西小哥还遇到好几个检查站——几个穿防护服的警察站路边,用黄色护栏把路一挡,就是个检查站。检查站外,警察会仔细盘问:绿码、核酸、当日车票,或有无其他必要出行理由。
走在路上,山西小哥觉得自己像是军营里负重越野的“兵哥哥”,只不过他掉队了,大部队消失不见,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。
“方舱大叔”要从宝山区跨越六十多里地到浦东机场,他一路换了好几种战略——徒步、电瓶车、共享单车等。途经区与区交界的地方时,他甚至要手脚并用,爬过铁丝网,并巧妙地躲过值守的警察。
检查站的警察,仔细盘问过路的人与车辆。/摄影:上海市民付先生
一开始,我会把这些故事想象成上世纪“谍战片”里的场景,实在没法与脑海中的上海对应上。直到越来越多上海人跟我讲述类似的经历,还给我看了实地照片,我才相信这些故事是如今上海普通人的出行日常。
在浦东机场“露营”是种怎样的体验?
如今的浦东机场正处在“战时”状态下——所有商铺全部关停,吃不上东西、外卖难进、车难打,所有人被迫最大化利用现有物资。
Mikey、“方舱大叔”与山西小哥,抢占了全机场最豪华的“总统套间”——即无印良品店门口的那张木椅。木椅长两米左右,没有把手,可以整个人躺上去。全机场仅此一张。木椅的延伸处,有个像迷你版榻榻米的地方,Mikey在上面铺了张瑜伽垫,作为他们的第二个据点。三人因此免于睡冰凉的地面。
Mikey与“方舱大叔”的豪华床铺。/摄影:飞温哥华的姐妹July
三人中Mikey的年纪最小,普通话跟英文也最好,因此包揽了他们三人的对外交流。他顺利地从飞走的旅客手中,拿到了充气睡袋、瑜伽垫等生存物资。他说,全机场就他们几个睡得最舒服。通常,滞留旅客从飞走的旅客那里继承他们的过夜装备,这些装备之后将流入“新来的人”手中,循环往复。
浦东机场的“轻奢套间”,是能躺的机场椅——本身能躺的椅子很少,更多是拿两排扶手椅并作一排来躺的。“轻奢套间”数量不多,极为抢手。资历深的滞留旅客,抢占“轻奢套间”的机会最多。幸存的极少数机会,只留给下一批来得最早的旅客。
两排并作一排的机场“轻奢”躺椅。/摄影:飞温哥华的姐妹July
当然,到机场早还不够,还要够“社牛”。浦东机场过夜,不欢迎“社恐”。
飞温哥华的姐妹July,提前一天中午2点左右就到了浦东机场。可她一进机场,惊讶地发现机场的两排“躺椅”上都睡满了人。她当即把整个浦东机场的机场大厅转了个遍,瞄准了一张没有扶手的软皮躺椅。椅子上当时还坐了人,她厚着脸皮凑上前去问,“你好,你们要过夜吗?”
没想到,她幸运地听到对方说他们今晚就走。于是,她开始在这张“躺椅”旁死守。半小时后,她看到机场里好的位置都被占完了,连最次的只能坐的椅子,都所剩无几了。
在这之后抵达浦东机场的旅客,要么占张椅子坐一晚,要么只能选“自助露营套间”,也就是睡地板。社交媒体上,输入“浦东机场过夜”,就能发现五花八门的“自助露营攻略”——如野餐垫配薄羽绒被;充气床垫搭配一次性野餐布;防潮垫配露营睡袋……所有这些,统称为“用过即弃过夜包”。
可实战之后,几乎所有人都会抱怨攻略欠佳——“床又冷又硬,被子就该带两床的”、“有充气床垫,就是太小了”、“感觉自己差一件羽绒服”等等。
社交媒体上的“浦东机场过夜攻略”
Nora是极少数“露营”体验颇佳的姑娘,过夜当晚,她将自带的两个行李箱拼成一张床——一个当枕头、一个搁身子。这样做的目的,一来免于躺在冰凉的地面,二来也是为了安全起见,“我身上所有重要的物品,都压在身下的两个行李箱内。”
她当晚的准备很全乎——穿着羽绒服、裹好睡袋,戴上眼罩、口罩、耳塞等,最重要的是,她与另一位同伴挑了个附近有工作人员,还有摄影头对着的角落,才敢安心躺下。
最近每天在浦东机场过夜的人流,少则几十人、多达一二百人。Mikey说,旅客聚集的机场出发层,能用的厕所男女各一个,打热水的地方,也只有一个。为了抢占稀缺资源,越靠近厕所与打热水处,睡的人越多。每天一大早,都会有人去厕所排队,女厕所尤其人满为患。
至于洗澡问题,Mikey住了半个多月机场,一次澡都没洗过。他也没功夫想这事。
因为即使有了“机场顶配”的露宿装备,也没有和之匹配的高质量睡眠。睡在“总统套间”的Mikey,为了防止猝死,强迫自己每天睡3个小时——凌晨3点在头顶射灯的照耀下,艰难入睡,早上6点准时被机场广播声吵醒。
但在浦东机场之外,那些露宿火车站外的人,只能蜷缩在过道处,连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。上海市民付先生亲眼目睹,在虹桥火车站外的流浪者把棉被一铺,就是张床,天一晴,就把棉被晾晒在附近的栏杆处。他们无处觅食和方便,连身为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“遮羞布”都无法维系。
火车站外,被滞留的旅客。/摄影:上海市民付先生
机场里的“集体野餐”
每天中午,浦东机场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推着一个卖泡面的货车经过。这时,几乎全机场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小货车吸引,争先恐后地凑上前来。
卖泡面的机场工作人员。/图源:微博
货车里的泡面只有一个口味——统一牌香辣牛肉面,没得挑,一个人只能买两桶。很多机场的滞留旅客,一天就靠这两桶泡面过活。Mikey说,更早之前,整个浦东机场连卖泡面的地方都没有。
不过Mikey他们三人是个例外,他们的泡面可以论箱买——不仅因为Mikey还在长身体,一天最多能吃八桶泡面,还因为他给机场抓到过小偷,立过功。
在机场偷东西的人,是位四五十岁的女性。某天,他亲眼目睹那位中年女性徒手拽开了上海某特产店的拉门,他看得目瞪口呆,“那个拉门只安了颗螺丝钉,拉垮得很”,他说,机场所有商铺的拉门,都是这个配置。理论上来说,只要你想拉,轻易就能拉开。
但当天,那位中年女性偷得实在有些过分——Mikey看见她拉了个皮箱,拼命往里塞,烟、酒、泡面、老婆饼、奶糖、酸奶、纸巾等等。最终,她一人提了四大皮箱的东西,旁若无人地走了出来。他说,“对方把店里的东西都拿了个遍,连装东西的皮箱都是店里的。”
她的动静实在太大,但除了Mikey之外,机场里的所有人都对此熟视无睹。Mikey跟这位中年女性有过结,早就想逮着机会整整她了。几天前,他在机场花500块钱点了份外卖——一盒酸菜鱼、四份炒饭、一份小酥肉、一个南瓜饼、五六瓶可口可乐等。他盘算着跟“方舱大叔”与山西小哥一起吃。可等他中途打了个电话回来,那位中年女性把还剩大半的酸菜鱼一顿乱吃,炒饭也被她吧啦了几口,对方还拧开可乐直接喝。听“方舱大叔”说,当时他们几个人拦她都拦不住。
Mikey当时一直饿着肚子,他吃不了辣,每次都要把泡面过一遍水再吃。吃到后面,一到饭点,他就感觉是去上刑,“怎么又饿了?”这次,他好不容易点了份外卖,结果没吃什么就被那位中年女性给糟蹋了。他被气得直跳脚。
当天,趁对方还在收拾的间隙,他跑去找了好几位安保打报告说,“离你几百米处的地方,有人正在偷东西。”可安保硬是没搭理他。无奈之下,他直接拨打了110。警察赶到了现场,人赃俱获。那位中年女性当天偷了五千块钱的东西,被关进了拘留所。Mikey摇身一变,成了机场的立功之人。
从那之后,机场工作人员经常会在给Mikey的泡面箱里偷偷塞些吃的,卤蛋、肉制品、面包、饼干等等。Mikey他们三人跃升为整个机场的“特权阶层”,“经常能吃到些普通人吃不到的东西。”
Mikey被投食的饼干、面包等。/摄影:Mikey
每天,Mikey还会跟新来的旅客边搭话边要点吃的。“方舱大叔”通常会借着交流“过夜攻略”的方式,跟他们换食物。他们也会从自己的库存里,拿出一些给没东西吃的旅客。
浦东机场内部,也盛行“物物交换”法则。Mikey会跟新来的旅客交换食物——基本就是交换不同口味的泡面、饼干、面包、咸菜等等,毕竟大家的食物都很有限。
饥饿,是所有浦东机场滞留客的共同记忆。每天早上醒来,Mikey第一眼就会看到无印良品货架上的零食,还有隔壁冰柜里的可乐、冰淇淋。他已经快忘了泡面、饼干、咸菜之外的食物,是什么味道的,他很想尝一尝。
他想不明白,为什么这些店铺宁愿白白开着冰柜、宁愿把东西放过期,都不愿把这些食物卖给他们?
可惜,他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,他离这些食物这么近,又那么远。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,反复提醒他:该吃泡面了!
只要能离开上海
白天,整个浦东机场分贝最高的声音,是循环播放的广播声:“温馨提示,请您全程佩戴口罩,并保持一米间距……”这段话Mikey在机场听了成千上万次,每次只要前奏声一响起,他张口就能背出接下来的话,“先中文念两遍,后英文念两遍。
广播会在白天多个时段循环播报,晚上也不能幸免,Mikey算了算,每十分钟就要播一次。每天早上,他都会被这个“催命”广播成功吵醒。白天,他也被吵得什么都干不进去,“连打一把王者荣耀,都不能打个痛快。”
机场里,正准备活动身体的滞留客。/摄影:Mikey
吃完饭,Mikey一时没戴口罩,立刻被机场内冒出来的工作人员抓住现行,“那个戴耳机的,快把口罩戴好。”
每次听到这个声音,Mikey心里的愤怒就会增长一点。他不明白,在这个地方,“你没有饭吃,没人管你。你没有水喝,也没人管你。你没地方睡,更不会有人管你。没人管你是死是活,但你不带口罩,就一定会有人管你。”
近一个月多来,浦东机场就像是整个上海的一个横截面。
但机场里的所有人,都不在乎戴不戴口罩,他们只在乎怎么逃出这里、什么时候才能回家?
Mikey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《荒野求生》里的“贝爷”,在玩一个生存挑战游戏。但在游戏里,“贝爷”至少知道明确的结束日期。不像他,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切?
机票被取消了20多次后,Mikey的情绪濒临崩溃,急需一个负能量宣泄的出口。在电话里,他跟我痛骂了三个多小时,尽情发挥了一个东北人的语言天赋。大部分时候,我只是听着,附和几句。
他还只有17岁,但却要面对这个操蛋的系统里最操蛋的状况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能竭尽所能让他骂得痛快。
他的心气很高,“你知道吗?我当时艺考连南艺、中传的复试都没去,我就要赌北电,结果我赌赢了。”可下一句话,他的心情立刻跌回谷底,“可没想到,我输了,输在回不去高考上。”
“14天内再回不去,我就要复读了,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复读的。我快疯了。”
聊到后面,他开始在机场散起步来,语气逐渐恢复平静。散步,是他在机场这段时间里唯一的解压活动。他说,他所在的那一层,从头走到尾,大概几十米长。他每天要来回走四五十圈。
散步时,他喜欢观察机场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他发觉在机场滞留越久的人,越喜欢把自己闷在一个角落,一个人对着一个屏幕,不说话、也不活动。“(他们都是)能不动就不动,因为动多了就会饿,饿了就要吃饭,吃饭就要花钱。”他对我说。
一个人躲在角落吃泡面的滞留旅客。/摄影:Mikey
Mikey说,唯一能让大家提起兴头的事,就是抢票,“赶紧离开这里,是所有人唯一的盼头。”
几天前,Mikey时来运转,买了张高铁票,成功逃到了杭州。现在,他正在杭州的酒店隔离,这次隔离至少要花费5000元。但他不在乎了,“只要能离开上海就好。”
他说,山西小哥也用这个方法离开了上海,估计现在也在中转地的酒店隔离。等隔离结束,他们应该就能顺利买票回家。
三人中,只有“方舱大叔”还待在浦东机场。Mikey说,“方舱大叔”听闻去中转地隔离要自费,就打了退堂鼓。他们俩都离开后,我对“方舱大叔”很不放心。所幸,Mikey跟我说,“方舱大叔”有个儿子,一直在远程为他打理一切。
“方舱大叔”还在执拗地等,等一班直飞家乡的航班、或是一辆能把他带回家的政府专车,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。我只盼望,近期要去浦东机场的朋友们,能为他多带点吃的去。
注:以上所有采访对象,均为化名;上述所有图片除特殊标注外,均由受访者提供。
//作者:Su
//编辑:Rice
//设计:板砖兮
//排版:sojulee
http://www.chushuping.com/chushuliucheng/